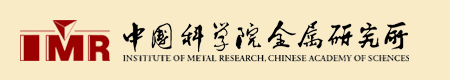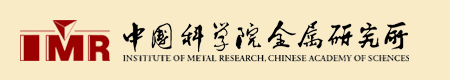一九四八年是解放战争关键性的一年,当时我家居住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长春。秋季,长春的国民党守军被解放军围困住了,城中粮食和燃料奇缺,物价猛涨,老百姓无粮可吃,饥饿的恐怖笼罩着全城。老师拿不到工资,常常罢教,终于停课。学生纷纷失学,我和弟弟,妹妹们也没能幸免,先后辍学回家。
家中七口人没有吃的,我流浪于街头。每天早晨我在重庆路一带的公共汽车站卖点报纸,有时还到停在站点的公交车上去叫卖。记得我卖的报刊中,有一种小报,刊名叫《漫画与漫话》,是有些进步倾向的刊物,其中好多漫画是讽刺国民党腐败和反对内战的,边卖边看一些,也从其中受到了不少教育,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有了一定的认识。
失学后,我曾在大经路的马路边摆个小摊,将家中的旧衣服、书籍、杂物等能卖的就拿去变卖,此时大家都很困难,也没有谁来买。书籍有时被路过的学生翻翻看看,有几本父亲的外文字典被人买了去,被当做卷烟纸,据说用字典纸卷的烟抽起来灰是白的,挺好用。在摆摊卖家里的东西时,由于自己年龄小没有经验,有人乘挑选货物之机,把其中比较值钱的父亲的一条西服裤子偷跑了,尽管家里的人没责备我,自己总觉得不好意思,还气得偷偷地哭了一场。
现在长春的二商店伪满时叫‘宝山’,是个高大的白色建筑物,解放前被国民党部队征用,当了存放军粮的仓库,在装卸粮食的过程中,总不免要散落一些米粒,我就和许多孩子去一粒一粒地拣,一天也拣不到一酒盅,那时粮食比金子还要贵重。解放军在城外围困得很紧,最后国民党兵也没粮可吃了,就只好依靠空运,一开始粮食袋子绑在降落伞上往下空投,有部分粮食顺风飘到城外,落到了解放军的辖区去了。后来干脆就直接往下扔,经常有人被砸死砸伤。粮袋落地摔的粉碎,粮食撒一地,常常被老百姓哄抢一空。当局为了防止被抢,三令五申的宣布,有敢抢军粮者,可以就地枪毙,而老百姓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反正饿死是死,枪毙也是死,仍然照抢不误。我也曾经抢过一次米,从摔开了花的米袋子里舀了一盆大米后,转身就跑了,大约有五、六斤。
我家七口人在这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朝不保夕,后来实在没办法了,父亲就找中学时期拜把子的老同学帮忙,托人把我和大妹妹、小弟弟送进了“战时难儿收容所”。实质上这是个相当于孤儿院的地方,地处长春二马路与大经路的交汇处。那里原来可能是个庙宇之类的地方,青瓦房,青砖墙,一个大院,临时收容了二百多个从四、五岁到十一、二岁的无家可归的孩子。这里的生活条件非常差,饥饿和疾病每天都在吞食着儿童的生命,死了的小孩就像一捆捆柴禾一样,被摆放在房后,待凑够一定数量时就由一位老大爷用手推车送走,扔到郊外去。每当夜里起来去房后小便时,看到冷色的月光照在死去的同伴们那苍白的小脸上,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心中暗想,不知哪天自己也会像他们那样躺在那里,一想到这些就感到非常恐怖,后来时间一长,觉得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因为这个收容所是临时建立的,连床都没有,大家睡在沿着墙根铺在地上的草垫子上。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姓陈的同伴,挨着我睡,第二天早晨他没按时起床,一叫他,他不动了,这时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多时了。在这里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对孩子们非常凶狠,动不动就动手打人,有个姓杨的管理人员,他打孩子时上面煽嘴巴,下边用脚踢,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四肢运动”。他那个凶恶的模样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不久,这个收容所的孩子越死越少,办不下去了,就把我们转移到西四道街的“博济孤儿院”。这是个以前就有的慈善单位,比收容所正规多了,但是死人的事儿也同样是几乎每天都有的,死因是饥病交加,由于吃的既少又差,还不卫生,大家体质特别虚弱,抵抗力极差,腹泻的时间过久时,直肠就会从肛门往外翻,翻出的直肠像尾巴一样,在身后拖着,翻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死亡。我也在劫难逃,脱肛也很严重,如果再晚几天解放,说不定我可能早在六十多年以前就到另一个世界做孤魂野鬼去了。
我和我的大妹妹、小弟弟同在这个“博济孤儿院”。有一天,我的大妹妹正在把头枕在桌子上休息,突然轰隆一声,一麻袋空运的粮食从天而降,砸穿天棚,砸碎了桌子,刮掉了我妹妹头上的棉帽子,吓得我妹妹号啕大哭,顿时屋内从天棚上落下的尘土弥漫,呛的人们无法呼吸。我闻声赶到时,看见几个国民党兵正在拖着麻袋往外走。吓得我妹妹的精神过了好久也难平静下来。
到了一九四八年末,长春城里的许多百姓纷纷都把家当卖掉,出卡子,差不多都走光了。听说在卡子外三不管的地方,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中,饿殍的尸骨堆积如山。我家人口多,不敢轻举妄动,抱着全家活就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块的念头,在饥饿的死亡线上作着最后的挣扎,硬着头皮挺了下去。
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守军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美式化装备精良的嫡系新七军,另一部分是杂牌军六十军。六十军本来是从云南过来的地方军,是被解放军打败后从吉林方面撤到长春的,外号叫‘六十熊’,像后娘养的一样,给养的水平比嫡系部队差一大截。一九四八年十月末,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守军司令郑洞国相继投诚,长春始告解放。
年终庆贺一九四九年元旦的时候不知哪位老兄为了显示自己横溢的才华,写了一付对联:“曾泽生泽及生灵方起义,郑洞国洞悉国事始投降”,这对联写的颇为巧妙,对仗还是满工整的,可是有人对此提出了疑义,并进行了批判,说长春的解放是解放军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不应该归功于曾泽生和郑洞国。这是后话。
解放的前一天,我和大妹妹,小弟弟三人回家,因家中无饭可吃,次日拂晓我们三人不得不返回孤儿院。二马路有一排用铁丝网钉在交叉的木头上做成的路障,是新七军和六十军防区的分界线,天太早,铁丝网还没打开,为了赶上早饭,三人就从铁丝网下面的空隙往六十军驻地的方向爬,正爬着,被一个国民党兵看见了,向我们喊了一声,随后就向我们的方向开了枪,一梭子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我们只好稍稍停了一下,趁他不注意,我们突然爬起来飞快地穿过了封锁线。我想,那个国民党兵是没想诚心打我们,只是想吓唬一下我们这些小孩子而已,要不然枪法再差,离得又那么近,也不会打不着。为了吃质次而量少的一顿早饭,险些把性命搭上,也实在是迫于无奈,这在当时是件很正常的事。
这天中午,我们从孤儿院的二楼走廊,看到邻院的六十军驻地在开饭,士兵们突然不听从当官的指挥了,把待分配的窝窝头哄抢一空,就估计是发生了什么变故。果然,夜里枪炮声大作,炸弹爆炸声震得我们的床铺乱颤,感觉眼睛所看到得东西都变了形,大家无处可逃,只好无奈地伏在床铺上硬挺着,听天由命。第二天清早出去一看,见到周围许多房屋被夷为平地,成为一片瓦砾场,老百姓死伤惨重,有一只苍白的手从炸弹坑的碎土中伸了出来,非常刺眼,令人毛骨悚然。原来是从沈阳来的国民党飞机来轰炸已经起义了的六十军,而六十军的驻地已经人走楼空,早就转移了,遭了殃的却是附近的老百姓。我们又拣了一条命。就是这样,长春在“血不沾兵刃”的情况下被解放了。
解放后,人民政府首先救济城中的老百姓,解放军进城后,把发给每个人二斤的小米送到每家每户,再三嘱咐让大家先煮粥喝,因为经过长期饥饿之后,是不能马上就吃干饭的,不然会因涨破肠子而死于非命。由于饥饿而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我们这些的老百姓被解放了,都从心里往外由衷地感谢亲人解放军的大恩大德。此后,伴随着时间流驶,生活也在不断地改善,瘦得不成样子的身体都逐渐在恢复了起来。
不久,我们兄弟五人就都回到大经路小学去上学,曾经一度失学半年多的孩子,又重新又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那种感觉真是用心花怒放来形容也不为过。面对这美好的条件,当然也是会加倍珍惜的。从此我们除了努力学习之外,我还积极争取要求进步,很快就加入了少年儿童队,(少年先锋队的前身),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学习上由于对自己要求得很严格,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在毕业时同期百余名同学中,按考试成绩排列名次也是名列前茅的。
我还踊跃地参加当时的各种社会活动。每当解放军解放了一座城市,我们就到大街小巷,用粉笔在墙上写“庆祝某某城市解放”的标语,进行宣传。学校组织秧歌队,到街上搞宣传庆祝活动,由于我个子高,常常是被安排在秧歌队最前头,扮演着手持锤头的工人角色,踩着锣鼓点,扭起大秧歌,既兴奋,又很惬意,从学校出发顺着大经路,一直向北,扭到胜利公园(此公园伪满时叫西公园,也叫儿玉公园,儿玉是个日本的高级军官,此时他骑着高头大马的铜像早已倒栽葱地被掀翻在石座的后面。)然后再扭回来,尽管身体很疲乏,但心里却非常高兴。不论是唱歌、演活报剧、表演霸王鞭等活动中都少不了我的身影。
共和国的建立,换了新天地。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联欢会上,我还演出了自编自导的节目,尽管水平不算高,大家也觉得挺精彩。从此,我们沐浴在党的灿烂阳光下,快乐地成长。
伴随着共和国的前进,我们也在前进。是党把我教育和培养成为一名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在科研的第一线经过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我在报纸上有过名,电台上有过声,电视上有过影,也曾经得到过不少荣誉。我把自己的青春无悔地献身给了国防科技事业。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转瞬之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步入了古稀之年。退休后,现在在家悠哉游哉地颐养天年,在和谐社会中过着有吃、有穿、有房住的幸福生活,与全国人民一起,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伴随着走向复兴的脚步声,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普天同庆、迎接我党九十周年华诞的日子里,我不禁心潮澎湃,想想过去,看看现在。过去的痛苦难忘记,今天的幸福说不完,抚今追昔,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