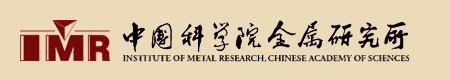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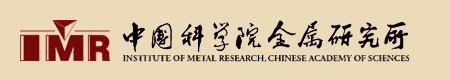 |
联系我们 | 了解金属所 |
 |
| 您现在的位置: 葛庭燧的科学人生 | 回到首页 |
| 深切怀念恩师葛庭燧先生 |
| 作者:王中光 | 2023-05-15 【大 中 小】【打印】【关闭】 |
|
2000年4月29日,葛庭燧先生在合肥走完了他87年的人生历程,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年,今年5月3日是他的90周年诞辰。我师从葛庭燧先生二十余载,从一个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在做学问和做人两方面深得先生的教诲,今忆往事,以寄怀念之情。 我1954年进入北京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专业学习。第二年学校决定在机械工程系设立“金属学和金属热处理”专业,由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李恒德先生任教研室主任,陈南平先生任副主任,并把我所在班的全体同学转到这个新设立的专业学习。为了使我们对这个专业有所了解,引发学习的兴趣,李恒德和陈南平先生曾召集全班同学进行了一次专业介绍。会上,我们问及两位先生,在这个专业领域里,是否有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两位先生介绍的第一位科学家就是葛庭燧先生及其享誉全球的内耗研究成果,并告诉我们,葛庭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葛庭燧”这个名字。虽然当时对“内耗”一无所知,但对先生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1959年9月我从北京清华大学毕业,来到金属研究所,在葛庭燧先生指导下工作。我第一次见到葛先生是在西大楼(今李薰楼)209房间他的办公室里。他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工作。于是,我谈起几年前李恒德和陈南平先生在清华给我们做专业介绍的情况,说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在他指导下工作。葛先生让我做的课题叫做“金属疲劳的物理原理”,他是课题组长,我是唯一的课题组成员。他说,裂纹的形成和扩展是金属疲劳的基本问题,如果能够有一种方法灵敏地探知裂纹,将避免因金属疲劳导致的灾难性事故的发生。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介绍了他关于这一研究课题的基本学术思想。他说,当火车到站时,总可看到工人师傅用小榔头敲打火车的轮轴等关键部位,他们是通过声音的变化用耳朵探知是否有裂纹等隐患的存在。他进一步解释说,当金属或金属构件中有伤时,它们的阻尼本领或内耗将发生变化,研究课题的目标就是通过测量疲劳过程中内耗或能量消耗的变化,揭示金属疲劳的基本物理过程,最终发展出比工人师傅的耳朵更灵敏的检测缺陷的仪器。他鼓励我大胆、主动和独立地工作,告诫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由于我对“内耗”和“疲劳”均知之甚少,葛先生除了指定一些基本文献让我学习以外,还亲自多次为我一个人讲课,介绍有关内耗的基本知识。他讲课,条理清楚,语言生动,又旁征博引,颇能引人入胜。他把我引到一个充满挑战的领域,我感到自己懂得太少,于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拼命地工作。葛先生提醒我要处理好“学习与工作”和“广与深”两个关系。他说,“学习要有目的,要结合工作的需要学习:知识面要广,只有这样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但工作要深,犹如挖井,挖得越深,泉水越清。”由于我的大学背景是工科,而研究工作需要扎实的理科基础葛先生除了为我单独讲课以外,还让我参加1960年3月由南开大学陈仁烈教授来所讲授的“金属电子论”的学习,参加1960年8月在长春主办的“位错理论全国学习班”。1961年,葛先生被任命为金属所主管研究生和干部培养的副所长,他除亲自为我们这些新参加工作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讲授“位错理论”以外,还组织以李薰所长为首的全体研究员,如师昌绪、郭可信、何怡贞、庄育智等先生和他本人,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分章讲授“金属学物理基础”。他还请来著名力学家胡海昌研究员于1962年4月来所讲授“线性弹性力学基础”,请来兰州大学张宏图教授于1963年2月来所讲授“晶体的范性及其理论”等。我参加了所有这些课程的学习,并参加了考试。通过学习,使我有了较牢固的金属物理方面的理论基础和较广博的专业知识,使我一生受用无穷。1960年,我们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题为“用测量能量消耗的方法研究金属中的疲劳裂纹”的文章。1960年秋天,由中山大学金属物理专业毕业的黄元士加盟课题组,我们通力合作,研究工作进展很快。1962年,我们先后在“物理学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6篇。葛庭燧先生为进一步培养我,于1963年提出让我做他的在职研究生,并制订了进一步工作的计划。但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我们的正有势头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延缓下来,我做在职研究生的提议也未获批准。1966年6月在全国蓬勃兴起的“文化大革命”更彻底打碎了我们的计划,摧毁了我们的梦想。葛庭燧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因“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我和黄元士也被卷入“革命的洪流”中,无心搞研究,直至1969年12月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0年葛先生获得“解放”,恢复了工作。从此他经常奔波于金属所与沈阳各工厂和鞍钢之间,参加技术协作活动,并写出“声发射”(1972),“全息照相与无损检验”(1973)和“磁粉探伤基础”(1975)等通俗读物。1972年7月我从农村回到金属所,安排在为培训新进所的转业军人和下乡知识青年而设立的“科技学校”,做一名数学教师,于是我与葛先生有了见面的机会。197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约我去他家谈谈,到他家以后,他说,“我们到外面散散步吧!”于是,我们俩沿着所内的南北马路,来来回回,边走边谈,而且主要是他谈我听。他说我们都应当回到研究岗位上去,但要换一个环境,具体讲,就是去北京物理所工作。他说他将向党委建议把我作为他的助手带走,如果不行,他将建议把我从科技学校调回研究室工作。我说,我非常感谢他的好意,但我认为组织上不会同意。他非常深情地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党委会接受我的建议的。”葛先生当晚同我所做的推心置腹的长谈,他对我的钟爱,一直铭记在我心中。1978年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葛先生的实验室得到恢复,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晶体缺陷与力学性质”研究室,我也回到了他的身边,负责内耗研究组的工作。当年所里决定给一批科研人员提职,葛先生向所里力荐破格提拔我,据说他在有所领导和各室主任参加的会议上,动情地介绍了我,赢得了与会者的理解和赞同。经科学院批准,我于1979年1月由研究实习员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随后经葛先生提名,我被所里任命为“晶体缺陷与力学性质”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初,德国马普金属研究所总所长Seeger教授邀请葛先生率三位青年研究人员去进行关于位错内耗的合作研究,我是葛先生选定的三位青年之一,但因政审不合格而没有出去。葛先生深情地安慰我,并表示一定要想法让我出国。由于我曾经管理过1975年由德国申克公司进口的试验机,解决过一些技术问题,而且成功地调试了该公司1976年销售给621所的一台试验机(当时外国人不允许进621所),得到该公司试验机部经理Jacoby教授的好评。葛先生在德国期间同Jacoby教授联系,要求他邀请我到该公司进行培训,Jacoby教授欣然应允。1979年9月我与621所顾明达和谢济洲一同赴西德申克公司进行为时两周的培训。培训结束后,葛先生又请马普金属所的材料所所长Diehlt博士邀请我去该所访问两周。我在那里见到了葛先生和何先生,以及李广义、孙宗琦和张进修三位同事。头一次看到一个中国之外的世界,感触万千,收获很多,但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我能出国了”,它打碎了因“出身不好”而长期套在身上的精神枷锁。 1980年9月,葛先生接受科学院的任命,前往合肥负责筹建固体物理所。他曾多次试图说服我去合肥,协助他工作。他曾严肃地对我说“我需要你现在的‘雪里送炭’,不是你将来的‘锦上添花’。”可是经过前思后想,我还是拒绝了葛先生的好意,决定留在金属所工作。1983年1月,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资助下,师昌绪先生派我去美国进修。在美国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一直保持同葛先生的联系,他还是不断劝说我去合肥同他一起工作。1984年8月我从美国回来,葛先生派固体物理所的办公室主任姜文学同志专程赴北京接我,并转达葛先生让我即去合肥一晤的口信。我当时没有能够马上去合肥,而是先回到沈阳。时任金属所党委书记的徐曾基同志得知此事后,致信姜文学同志,批评他“此举形同绑架”。我最终没有去合肥,曾使葛先生伤心和失望,但他丝毫没有怨恨之意,一如既往地关心和信赖我,任命我为“内耗与固体缺陷开放研究实验室”学委会副主任、委员,邀请我参加固体所一些重大活动。1988年,国家计委批准在金属所建立“材料疲劳与断裂”国家重点实验室,我被任命为实验室主任,1990年和1992年这个实验室在全国评估中连续两次评为优秀。葛先生对我们取得的成绩表示赞扬。同时对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提出建议。在1993年7月20日的来信中说,他对“晶界弛豫引发微裂纹的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并说他的框架思想“远在40年代就与Zener教授讨论过”,但固体所“人力有限,困难不少”,希望我们能做这方面的工作,还告诫说,“不能操之过急,一个好的构思是需要积累的。”我们此后进一步安排了一系列研究晶界疲劳裂纹的工作,并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我曾多次邀请他回金属所看看,参加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会议,指导我们的工作。1994年12月18日他终于来信说,“承你多次邀请,希望明年五月成行。”并建议邀请我们的老伙伴,1973年直接由农村调回广州中山大学工作的黄元士教授以来宾资格参加学委会会议。1995年5月8日,葛先生以82岁高龄第一次回到他离别了15年的金属所,被特邀参加我们实验室的第二届学委会第三次会议,黄元士教授也应邀回所。葛先生的到来受到了以李依依所长和董文华书记为首的金属所领导和众多金属所同仁的热烈欢迎,他不仅对我们实验室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而且在全所“春季青年学术报告会”上,结合他的人生经历,向青年科研工作者和研究生做了“爱祖国、爱科学”为主题的报告。葛先生对我当年未跟随他去合肥的理解和对我的工作的一贯热情支持,使我深受感动。葛先生一直怀有我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希望和信心,他不仅自己主动做我的推荐人,而且还联合著名力学家李敏华先生和著名疲劳专家颜鸣皋先生推荐我。他对我每次上报的材料都精心审查和仔细修改。 葛庭燧先生一生“热爱祖国,情系中华”,有关这方面不乏感人的事例。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清理阶级队伍”中,葛先生因“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我们研究室因“特嫌”问题而被审查的泰国归国华侨李柏年。在隔离审查中,他们不仅受到精神的折磨,还受皮肉之苦。有一次,李柏年见葛先生唉声叹气,就偷偷地问他:“老葛,你要是当年不从美国回来,今天就不会受这份罪了。”葛先生回答说:“我不后悔回国,就是死,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死在中国。” 我已年近古稀,要学习葛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和“老牛自知夕阳晚,无需扬鞭自奋蹄”的可贵精神,为发展科学事业发挥最后一份光和热。永远缅怀恩师葛庭燧先生! (本文发表在2003年《金属之光》第21期)
|
| 文档附件 |
中国科学金属院研究所 版权所有 辽ICP备05005387号-1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72号 邮编: 110016 电话: 024-23971507 |